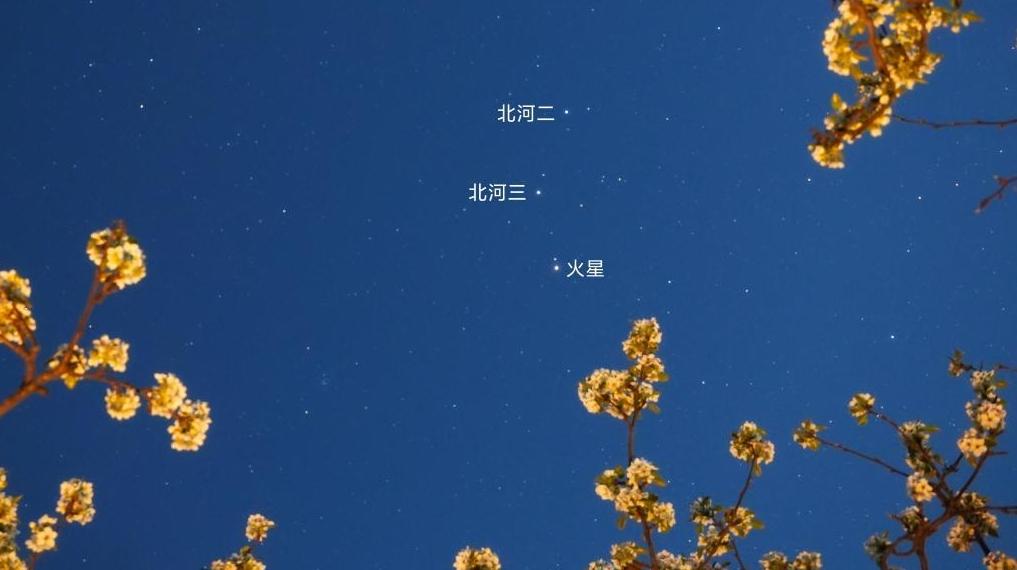科技日報記者 陸成寬
又是一年清明至。在這個慎終追遠的時刻,我們深切緬懷那些為共和國科技事業鞠躬盡瘁的先輩。
去年清明至今,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的已故院士名單上,又添了34個名字。他們用畢生心血澆灌科技報國理想,斯人已逝,幽思長存。面對這些離去的國之棟梁,我們以文字遙寄哀思。
一年來故去的34位院士中,周光召是唯一的“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
1999年,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隆重表彰為我國“兩彈一星”事業作出突出貢獻的23位科技專家,并授予他們“兩彈一星功勛獎章”。時年70歲的周光召位列其中。他為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和氫彈的理論設計作出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貢獻,領導完成了裝備部隊的第一代核武器的理論設計工作,為我國掌握中子彈和核武器小型化設計技術、完成核武器從第一代向第二代的過渡奠定了重要基礎。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周光召是位傳奇人物。在蘇聯留學時,28歲的他指出了蘇聯專家的錯誤,最先提出粒子螺旋度的相對論性;1960年他簡明地推導出贗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PCAC),成為國際公認的PCAC的奠基者之一,年紀輕輕便在國際物理學界贏得了聲譽。
然而,1961年回國后,周光召卻從公眾的視野中消失了,開始了一段“干驚天動地事、做隱姓埋名人”的波瀾壯闊的人生。當蘑菇云在羅布泊騰空而起時,大家才發現,他將最美好的年華獻給了祖國的國防事業。
在這些已故院士中,還有三位院士的身份非同尋常,都曾榮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他們是黃旭華、王永志和張存浩。其中,黃旭華、王永志還曾被授予“共和國勛章”。
與周光召一樣,黃旭華也曾是一位為國鑄重器而隱姓埋名的人。2020年榮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之前,鮮有人知曉他的名字。作為共和國第一代核潛艇總設計師,從1958年到1988年,黃旭華遠離家鄉、隱姓埋名,踏上艱辛求索路。
因為工作保密,黃旭華整整30年沒有回家,甚至父親、二哥逝世也不能奔喪。離家研制核潛艇時,他剛三十出頭,等回家見到親人時,已是六十多歲的白發老人。30年間,他組織、協調解決了第一代核潛艇研制各階段的重大技術難題,成功執行核潛艇水下發射導彈試驗任務。
研制戰略導彈,研發運載火箭,送中國人上太空并籌建中國空間站——王永志曾說,“一輩子就干了三件事”。
作為我國載人航天工程的開創者之一和學術技術帶頭人,王永志始終將祖國的需要作為自己前進的方向,不僅讓中國擁有了抵御外敵的國防重器,也讓國家擁有了運輸衛星的巨擘天梯,更讓中華民族實現了千年飛天夢想,同時也為中國載人航天未來事業打下了基礎、鋪平了道路。
說起張存浩,人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排除萬難回到祖國,一生為國家戰略所需多次改變科研方向。他曾說:“我一輩子為了國家轉行多次,放棄自己的科研興趣,我從不后悔。我回來就是為了報國的。”
張存浩長期從事催化、火箭推進劑、化學激光等領域的研究,取得多項國際先進成果。比如,他在國際上首創研究極短壽命分子激發態的“離子凹陷光譜”方法,并用該方法首次測定了氨分子預解離激發態的壽命為100飛秒,該成果被《科學》主編列為亞洲代表性科研成果之一。
在34位已故院士中,常印佛是唯一一位兩院院士。他是著名礦床地質學家,畢生從事礦床學、礦產勘查學和區域成礦學研究,在區域成礦、礦床研究、找礦勘探領域成果突出,為我國礦產資源開發和地質勘查事業的發展作出重大貢獻。
常印佛于1991年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后稱院士)。1994年,中國工程院成立之初,常印佛又因具有較強的工程背景,而被聘任為中國工程院院士。像常印佛這樣一人身兼兩院院士的,在中國只有34人。
一年來逝世的34位院士,多已到耄耋之年。
百歲院士兩位:戴立信、裴榮富;“90后”院士25位:陳俊武、韓禎祥、汪耕、宋家樹、張存浩、沈緒榜、周光召、田昭武、邢球痕、邱大洪、高鎮同、李德平、常印佛、金慶煥、邱蔚六、朱永(貝睿)、王永志、張壽榮、林尚揚、葉銘漢、施仲衡、黃旭華、姚穆、趙法箴、汪懋華;“80后”院士6位:萬惠霖、白以龍、程順和、陳景、劉昌孝、王正國。令人痛惜的是,還有一位“70后”院士過早地辭別了中國科技界,他就是中國工程院院士孔憲京。
他們或攀登重大原創的科學高峰,或攻克“卡脖子”關鍵核心技術,或開辟新賽道為新學科奠基……生命的時鐘雖已停擺,但是他們的學術造詣和科學精神將永遠留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