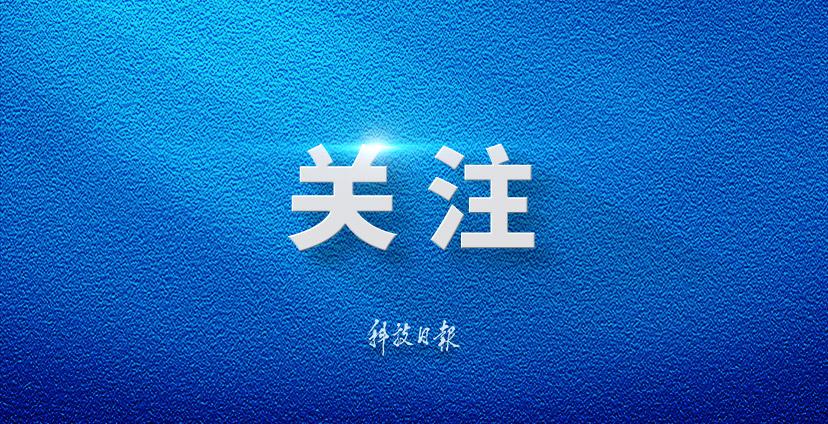科技日報記者 金鳳
端午期間,想感受曠古爍今的城墻古韻,南京城墻博物館是個不錯的去處。你可以駐足多媒體沉浸式影院,以第一視角身臨其境地穿行于明朝首都南京的街肆弄巷,也可以站立在四重城垣沙盤旁,跟隨多媒體立屏和投影,感受明初南京四重城垣環套的宏大城市格局。
始建于公元1366年的南京城墻,作為現存體量最大的城市城墻,是南京留存至今重要的文化遺產。這份文化遺產,如今被文物保護工作者們借助地理信息系統、三維數據采集、三維建模技術等數字技術,生成數字檔案,留存“DNA”信息。
在保護中發展,在發展中保護。650多歲的南京城墻,如今也擁有一批特殊的“醫生”。20多公里的城墻分布著263套自動化監測設備,它們實時捕捉城墻本體上發生的毫厘變化。
風云際會650余年,如今的南京城墻正借助數字技術“延年益壽”。
數字技術加持,構建城墻“一張圖”
南京城墻全線的最高、最低點在哪里,最寬、最窄處位于哪一段,城墻上有哪些病害、銘文,如今都可以在南京城墻數據資源管理平臺,找到答案。
“你看,城墻的矢量底圖、遙感影像、歷史地圖、城墻精細模型、點云數據、BIM數據、360度全景數據,以及大環境數據、南京城墻分段示意圖、歷代城門匯總圖層等各種數據都可以在這里查詢。”隨著南京城墻博物館副館長金連玉敲擊電腦鼠標,南京城墻數據資源管理平臺展現在記者眼前。

圖為南京城墻博物館。
金連玉介紹,為了摸清城墻家底,自2017年起,南京城墻保護管理中心(以下簡稱管理中心)先后啟動南京城墻磚文數據庫、南京明故宮大遺址文物數據信息采集以及南京城墻“一張圖”——南京城墻數據資源管理平臺建設(以下簡稱城墻數據平臺)等數字化項目。
“對于城墻文物現狀信息的提取,主要通過采用三維激光掃描、無人機傾斜攝影以及三維建模技術進行采集。”金連玉說,借助數字技術,管理中心對南京城墻180866塊銘文城磚,明故宮大遺址現存300余件不可移動、可移動文物,以及南京城墻本體及周邊環境均進行測繪、掃描、建檔、建庫,為明故宮大遺址、南京城墻建立了最早、最完整的全維度數字化文物檔案。

從高空俯瞰南京中華門城堡及南京城墻博物館。
記者在平臺界面看到,城墻本底數據涵蓋南京城墻全線城墻本體精細三維模型數據,以及南京城墻全段20處360度全景數據等信息;周邊大環境數據;14幅1898年至1948年南京歷史地圖;20套亞米級遙感影像數據;本體病害等多個數據庫,則收錄了2019至2021年的南京城墻沉降變形監測數據、18萬余條城磚銘文數據、453萬余條病害監測數據等多維信息。
文物遺產信息一目了然的同時,平臺還能進行城墻緩沖區分析、模型剖面分析、淹沒分析。
“例如淹沒分析,可以分析當水位漲到一定高度,城墻將被淹沒到什么程度;另外,文化遺產保護有保護范圍和建設控制地帶,在建設控制地帶,建筑物的高度建設到多高,才不會對城墻造成影響,都可以在平臺里模擬出來。”金連玉說。

圖為南京城墻博物館。
20余公里設置1575個監測點位,為城墻體檢
如何讓650多歲的南京城墻戰勝時光的打磨“延年益壽”,也是當下城墻保護者的歷史使命。
跟隨南京城墻監測預警中心數據采集專員田野步行至南京中華門城堡旁的赤石磯登城口,只見一條長約5米的細長管線從城墻頂部緊貼著城磚垂落下來,在它旁邊,還有一根細細的金屬管,附著在相鄰的兩塊城磚上。
“這就是多維度變形監測計和測縫計,它們每隔幾個小時,會將城墻的位移、溫度等數據傳回后臺,如果有異常,系統會提示,巡查人員會到現場實地踏勘排除隱患。”田野說。

在南京中華門城堡旁的赤石磯登城口附近區域,多維度變形監測計和測縫計正在監測城墻“體征”。科技日報記者 金鳳 攝
依托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和通信技術等數字技術,這些“體檢儀”中傳出的數據,最終接入南京城墻監測預警中心。
在登城口不遠處的南京城墻博物館地下二層,一張鋪滿整面墻的大屏幕,便顯示著城墻不同監測點位的回傳數據。
田野介紹:“監測預警平臺通過安裝的263套自動化監測設備、1575個監測點位,對城墻本體位移、膨脹、沉降、裂縫等數據及時采集并分析,監測城墻本體及周邊環境的實時變化,可以實現‘變化可監測、風險可預報、險情可預控、保護可提前’的預防性保護,筑牢了城墻本體安全防線。”
無論是探清城墻“家底”,還是搭建監測預警平臺,數字技術的運用,為南京城墻的保護和利用筑牢了安全防線。
“數字技術是實現文化遺產科學保護及展示利用的重要手段。我們希望利用數字技術在文物信息留取、遺產健康監測、展示利用等方面,保存珍貴遺存與遺物信息、監測遺產本體風險、發掘與展示遺產價值。”金連玉說。
(文中圖片除標注外均由南京城墻博物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