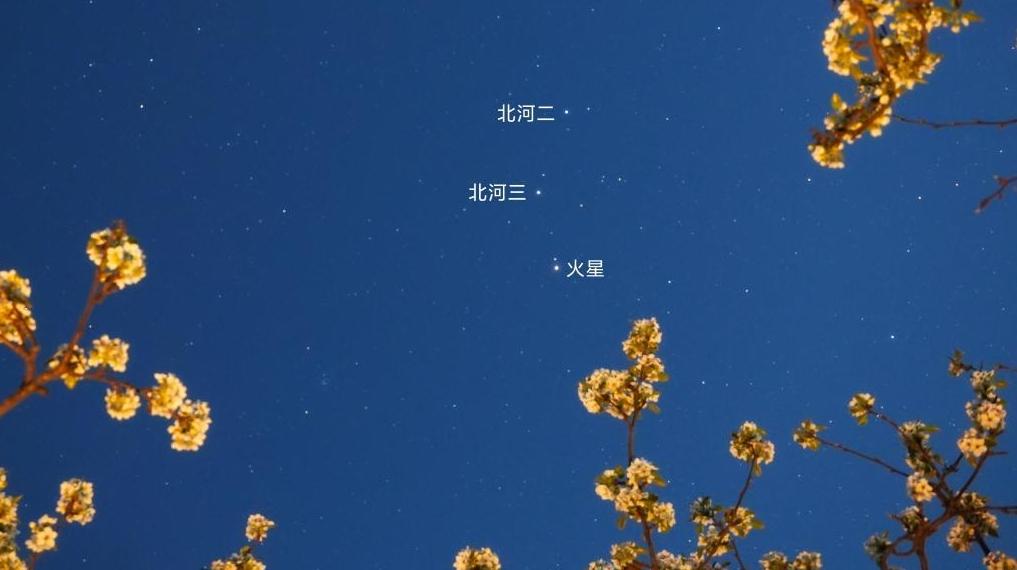巍巍賀蘭,遠山如黛。這里日照時間長、太陽輻射足、晝夜溫差大、空氣濕度低,是世界公認的黃金奶源帶。
2023年12月,坐落在賀蘭山腳下的寧夏農墾乳業股份有限公司平吉堡第三奶牛場傳來好消息——該奶牛場單只奶牛產量(以下簡稱單產)提高至每天38.37公斤,年平均單產突破14噸,同比提升7%,達到全國領先水平。
“十四五”期間,寧夏回族自治區定下了全力打造“高端奶之鄉”的目標,以寧夏農墾乳業股份有限公司為代表的寧夏乳企共同推動產業高質量發展,讓寧夏奶源地的名頭更響亮。
近日,寧夏農墾乳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畜牧師郝峰接受科技日報記者采訪,講述了畜牧業科研人員自主創新、勇攀高峰的不凡歷程。

靠科技創新提高奶牛單產
記者:提到寧夏特色農業,大家會想到枸杞、葡萄酒等。但很多人或許不知道,這里還是我國重要的黃金奶源基地。
郝峰:是的。寧夏地處北緯38度,是農業農村部確定的全國牛奶優勢產區。許多知名乳品企業都在寧夏建廠。
記者:寧夏牛奶產業發展情況如何?
郝峰:我給你看兩組數字。
2022年,寧夏奶牛存欄83.7萬頭,同比增長19.2%,增速連續4年居全國第1;生鮮乳產量342.5萬噸,居全國第4。
2023年上半年,寧夏奶牛存欄88萬頭,生鮮乳產量204萬噸,居全國第3。寧夏奶業總體表現還是很搶眼的。
記者:這么看,寧夏牛奶產業正“行駛”在快車道上?
郝峰:從產量來看,確實如此。但評價牛奶產業的發展水平,不能只盯著產量,還要看增量是如何實現的。
一般來說,我們提倡“用最少的牛產最多的奶”,盡可能靠科技創新提高奶牛單產。不過,目前許多地方是“養更多的牛、產更多的奶”。我覺得這是不科學的。
記者:您最早想到了哪些提升奶牛單產的方法?
郝峰:我平時比較關注國際前沿科技。2001年,我偶然在一本國外雜志上看到,提升奶牛飼喂效率的最優方式之一是全混合日糧(TMR)飼喂技術——把青貯、啤酒糟、稻草等和勻了給奶牛吃。
記者:給奶牛單獨吃精料不好?
郝峰:精料在奶牛胃里發酵速度非常快,可能把牛脹死。過去,許多農戶以為給奶牛大量喂精料可以提升產量,結果導致奶牛死亡,造成了經濟損失。
于是,我嘗試在牧場應用全混合日糧飼喂技術和奶牛分群飼養技術。應用前,公司奶牛的單產約6噸。應用這兩項技術的次年,奶牛的單產就達到了8噸,目前已經突破13噸。
記者:新技術推廣起來順利嗎?
郝峰: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應用新技術是對傳統方式的變革。推廣過程還是比較艱難的。
例如,在推廣全混合日糧飼喂技術時,起初在沒有專業攪拌設備的情況下,我們采用人工拌料的方法:鋪一層青貯,加一層精料,再加一層啤酒糟,最后人工再翻一遍。
當時,這種方式遭到了許多人的反對。他們認為“這是瞎胡鬧,效率太低了,沒見過有這么喂牛的”。我不厭其煩地跟他們解釋,并堅持做下去。
后來,隨著單產的提升,工作成績得到了寧夏畜牧工作站領導的肯定,相關技術才得以在寧夏得到快速推廣。
投身智慧牧場建設
記者:糞污處理是不是奶牛場普遍面臨的難題?
郝峰:對。截至目前,奶牛場糞污處理問題依舊沒有最優的解決方案。從2015年開始,我嘗試用各種方法解決這一難題。
記者:您具體是怎么做的?
郝峰:我承擔的第一個環保項目是“農墾奶牛養殖場綜合環境管理示范研究”。接下任務后,我沒有沿用傳統的達標排放技術路線,而是采用了生物技術來處理牛糞水。
具體來說,我讓牛糞水變成了生物肥料。它不但能夠代替部分化肥,還可以把有益的微生物帶入土壤,起到改良土壤、提高農作物抗病能力的作用。
記者:聽說您還參與了寧夏智慧牧場建設?
郝峰:是的。如今,5G、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賦能智慧牧場,中國畜牧業正向數字化、智能化加速轉型。科研人員要積極投身到轉型發展中,為產業轉型貢獻力量。
2014年至2021年,在有關部門的支持下,我帶領團隊成員先后承擔了多個國家科技支撐項目、寧夏重大科技項目,自主研發了多個物聯網自動化設備和智慧管控平臺。比如2022年,我們在全國率先研發出移動犢牛智能飼喂系統。該系統目前已經在全國推廣應用。
記者:這是一個什么樣的系統呢?
郝峰:以前,犢牛每頓吃多少,全憑飼養員經驗。移動犢牛智能飼喂系統可以根據犢牛月齡匹配適宜的飼料量,還可以分階段提示飼養員犢牛喂養的要點。自從啟用這個系統,犢牛吃得飽、吃得好,增重指標完全達到預期。
記者:像這樣的“神器”還有什么?
郝峰:比如,我和團隊成員研制的奶牛活動量無線采集器,可以監測奶牛發情活動、健康狀態以及在采食位停留時間;研發的奶牛體型鑒定和飼料配方軟件等,提升了寧夏牧場奶牛生產性能測定(DHI)水平和信息化管理水平;研制的奶牛環境檢測裝置,可以自動采集奶牛場空氣溫濕度、甲烷濃度等數據,自動控制牛舍內風機和噴淋裝置的運轉……
記者:最近您和團隊在做什么?
郝峰:這段時間,我和團隊成員正在進行國產擠奶機控制系統的研發工作。目前我國擠奶機控制系統都是進口的,我們無法完全獲取相關數據。數據價值得不到充分挖掘,智慧牧場建設就缺少關鍵支撐。
另外,國外設備非常昂貴。我們想設計出更適合中國牧場的設備,提升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成本。我們與國內外專家組成聯合攻關團隊正在啃這塊“硬骨頭”。
注重攻關意識和敬業精神
記者:目前我國牛奶產業的人才發展狀況如何?
郝峰:近些年,從寧夏到全國,牛奶產業發展都非常迅速。但有一點我們必須意識到,整個產業缺人,更缺優秀人才。特別是在西部地區,這種情況更嚴重。我們這里引才工作難度比較大。
同時,伴隨智慧牧場建設的加快,牛奶產業還需要物聯網、人工智能等領域的研發人員,特別是復合型人才。
記者:既然“引才”存在難度,那么“用才”就顯得格外重要。您是如何培養團隊的?
郝峰:平心而論,我們團隊里特別拔尖的人不多,碩博士占比不高,很多成員是一線技術人員出身。但就是這樣一支隊伍,取得了一系列創新成果,備受業界關注。為什么?這得益于我們團隊內部的氛圍——每個人都毫無保留地分享自己的經驗,讓其他人少走彎路。
在我們團隊里,如果你學會了一項技術,害怕別人從你這里“偷走”,那么對不起,這里不歡迎你。通常我引進了一項新技術后,會先教會幾個人,然后學得好的人帶領其他人學習。
除此之外,在技術研發方面,我沒有給團隊成員設定特別具體的指標。大家可以根據實際需求或興趣,選擇自己的方向。
記者:這種寬松的管理方式是否會影響效率?
郝峰:也有人說,現在應實行量化考核,讓大家全憑自覺,很難行得通。但我的觀點是,科研工作具有特殊性,技術創新需要寬松的環境。把人管得太死,他們的思想容易僵化。
記者:結合個人成長經歷,您認為應著重培養青年人才的什么品質?
郝峰:我認為,需著重培養青年科研人員的攻關意識及敬業精神。我的理念是,干一行就要愛一行,愛一行就要謀一行,謀一行就要鉆一行。生命不息,科研不止。作為公司總畜牧師,我常年帶著團隊成員“泡”在寧夏多地的奶牛場。遇到問題我們就潛心鉆研,吃再多苦也不放棄。
記者:您能舉個例子嗎?
郝峰:拿我帶隊進行奶牛場糞水處理研究的經歷來說吧。2015年,接下任務時,我們在這個領域幾乎沒有任何積累,可以說是從零開始。我們不顧糞水的臟與臭,不放棄任何一個可行技術,在多個牧場開展了生物除臭技術、生化處理技術等的驗證工作。
說實話,這項研究并不輕松。為了評價除異味效果,我們就把各種臭水裝瓶,然后挨個聞,記錄分析后再找改進的辦法。令人欣喜的是,如今我們已經初步建立了一套奶牛場糞污處理與資源化利用及生態種養循環模式。
記者:您認為寧夏牛奶產業當前還存在哪些短板?
郝峰:短板不少,人才、技術都需要加強。另外,在政策方面,需要有關部門因地制宜制定出更好的發展策略。
記者:您覺得我們該怎么利用好“外援”?
郝峰:對寧夏來說,“請外援”這種方式很實用。我做胚胎移植的時候,就請來了國內該領域的先進企業——北京八零同創技術有限公司的技術團隊。后來,我們團隊在研發微生物技術時,引進了中國農業大學的科研力量。
有一點需要指出,與外部合作,很多人干脆就是“拿來主義”。我覺得,這樣不妥。
我理解的成果轉化,是先實打實地“拿來”。在這個基礎上,本地科研人員要根據需求進行消化、吸收、創新,最終把技術變成自己的。這樣操作的好處是,技術成果真正得到了轉化,即便合作中止,自己也能干。
記者手記
從銀川市內的家出發,開車一路向西。掠過城市、鄉村,在一片積雪皚皚的田野旁,有幾間不起眼的平房。
那便是郝峰上班的地方。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這條路,他義無反顧地走了33年。
郝峰說話很穩,但說到技術創新,語速會明顯加快。在他內心深處,憋著一股勁。
上世紀60年代,牛奶還是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奢侈品。那時,賀蘭山下的戈壁灘上就有了寧夏農墾平吉堡奶牛場,這是郝峰所在公司的前身。郝峰的前輩們從內蒙古大黑河奶牛場引進了20頭三河牛,從北京北郊農場引進了106頭黑白花奶牛,并在這里立下宏愿,要讓牛奶“飛入尋常百姓家”。
如今,接力棒交到郝峰手里,科研人員的目標變成了“自主創新”。郝峰說養牛太苦了,看到這么多設備都依賴進口,覺得很辛酸。
他要改變。
從少年到中年,郝峰鉚足了勁在飼料、營養、繁育、擠奶和環保等方面研發、推廣多項實用技術,不斷降低生產成本和投資成本。
前些日子,寧夏普降大雪,城里的雪早都化了,郝峰所在的牧場依然銀裝素裹。郝峰說,工作累了出來走走,頓覺天地遼闊、精神振奮。他要在皚皚白雪之中,踏出一條新路。
(科技日報記者 王迎霞)